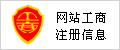临近新年的上海踩踏事件又让我们反思中国超大城市的问题,仅有光鲜亮丽的高楼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意味着好的城市治理,治理的现代化更多体现在软的方面,这些超大城市的经济水平基本都超过一万美元,治理的重心应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和环境领域,包括生态的保持和改善。
超大城市的增长极限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显著特征是大城市化,特别是特大城市的高速规模扩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特别提到“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社科院最新一期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也将焦点聚焦在特大城市这一矛盾。国务院最新发布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提出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等新形势要求,因此重新调整了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并增设了“超大城市”,标准为城区的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全球此类城市共有25个。
根据国内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有6个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超过1000万,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和深圳,10个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超过500万,21个城市市辖区人口在300万到500万之间,164个地级市市辖区(或县级市)人口在100万以上。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综合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相关统计数据比较见表1),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不足,在生态环境领域则突出表现在雾霾、缺水/内涝、垃圾围城三大问题,大气、水、固废全线告急,超大城市的生态治理显然需要新思维。

超大城市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似乎要比人口、经济、土地、能源的发展先达到极限。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在超大城市及其周围经济圈中尤其明显,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最近完成的《基于全国城市PM2.5达标约束下大气环境容量模拟》初步核定表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大约有80%以上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超标,其中京津冀地区为严重超载区域,北京和天津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的超载率大于150%,氨的超载率大于100%。另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与可持续消费研究报告》表明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和深圳的人均生态赤字都高于1.4全球公顷,意味着其消耗的生态资源需要超过1.4倍的区域面积才能提供。
超大城市的治理困局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超大城市都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全国要素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是超大城市高速发展的原因,也是超大城市不可抑制的规模诅咒的由来。超大城市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征用外部资源和环境容量来维持其规模,比如水资源和电力外调、垃圾外运、污水外排等,其自身已不是一个自我平衡、自我调节、可持续的完整生态体了。
超大城市的规模控制目前主要通过户籍制度来实现,限购、限行等措施都是基于户籍政策来划分的,但单纯依靠此类行政手段似乎总被人们诟病,认为其不是现代治理。就像物业管理,聪明的管理员通过电子监控、信息登记、代收等方式应对电商时代越来越多出入小区的快递人员,而懒惰的管理员则通过一律不让快递员进入小区来实现所谓的安全,要接快递只能出来自取,如果你是“剁手党”,肯定对后者深恶痛觉。前段时间北京官员排斥外来人口的言论就广受批评,而深圳突击出台小客气限购政策也备受争议。
当前有效的方式就是通常我们所熟知的经济手段,提高超大城市公共服务价格,比如高地铁票价、高停车费、高房价、高水价和电价等,通过价格杠杆,自然挤出低效的产业和低收入人群,但这当中又存在着加剧社会不公平的倾向。行政手段对增量更不公平,新进入城市和后发展的群体受到限制,这也是除上海外北京和贵阳的小客车限购令都采用摇号而未采用竞价的原因,广州、天津和深圳则采取了摇号和竞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平衡;而经济调控则对存量中的弱势群体更不公平,且这样的调控手段需要与替代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相配套,比如北京地铁提价仅在高峰期下降了约5%的流量,其效果非常有限。发展到当前阶段,超大城市的治理应该有个基本限度,那就是要改善城市内的公平,至少不是加剧和扩大现有的不公平。
中国超大城市的生态问题,并不同于欧美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案例,其问题的症结和影响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其人口和地理的规模效应,加之近十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狂飙突进和高度同构化,污染物排放的增量和增速都和经济表现一样让世人瞩目,其最终导致的雾霾受灾人口近十亿、受灾面积上百万平方公里,都是当年伦敦和洛杉矶的大气灾害无法比拟的。
我国2000年起就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近期又陆续发布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重点工程项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地方实施细则等。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城市污染排放清单和治理措施看,思路无非针对本地污染源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即去工业化和限城镇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
去工业化核心是去煤化,直观的表现是加快淘汰和搬迁落后产能“三高”企业,集中完成部分留存城市中的燃煤电厂、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实现主要城市的煤改气、煤改电等。限城镇化的主旨是控制消费排放规模,主要手段限购限行,特别是严格控制机动车的保有量和限制出行,同时辅以油品质量的逐步提升。去工业化主要针对社会大组织,限城镇化主要针对普罗大众。从目前短期治理效果来看,传统行政和强制手段对社会大组织较为有效,但究其实质只是原有系统性问题的“补丁”,不是所谓的“升级版”,从而并不能产生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和生态变革。中国超大城市生态治理,面临新的阶段和条件,需要在理论和实务上进行创新,特别是在生态治理市场化和大众化方面。
超大城市的绿色秩序
近年来面对房市下行压力,47个限购城市中已有42个陆续取消限购,应该说,限购和取消限购都是极其简单粗暴的。当前有4个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仍然采取限购措施,想放松政策但仍有顾虑,其实这几个现代化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完全可以换一种思路来治理,那就是构建新的绿色秩序。这在部分城市的小客车限购令中已有突破,比如北京、深圳的节能与新能源车增量指标和普通车增量指标分别摇号,前者的中签几率更高。这就使得行政和经济手段之上有了生态效率协同的正当目的,这样的区别政策同样可以与房产限购相结合,比如绿色建筑的限购可以放松。即使同样存在经济购买力上的不公平,但这种购买行为产生正的环境外部性,是全市人民都获益的。
进一步构建以社会绿色信用为切入口的新型治理模式,将传统行政规制手段有效转化为信用管理和市场交易,会使得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消费模式得到合理的控制。以机动车限牌、限购、限行为例,如果实行绿色信用支付(比如可以用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扣拍卖和竞价的部分金额)或绿色等级排序(比如绿色信用累计到一定水平可以享受优先购买)来重新定义该政策,即使不一定促进节能与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但整个城市完成了减排,这样的政策体系不仅解决城市管理问题,也创新生态治理,形成现代城市治理的绿色公平秩序。该信用体系还可进一步与以企业为主体的排污权、碳排放权、节能量等交易市场进行连接,形成更大的社会效应和市场规模。
现有的房产和汽车限购政策作为社会绿色信用体系的切入点将大大提升绿色金融市场的活跃度,并进一步带动民众参与城市生态治理的意识。以汽车限购为例,上海早在1994年就开始对新增的客车额度进行总量控制实行拍卖制度,车牌拍卖资金年收入近年来已经超过60亿,即使以拍卖额度的10%计以碳信用进行抵扣,光上海市场2015年就可能超过10亿的市场规模,高于当前全国7省市碳交易试点2014年全年成交额。去年6个超大城市房产和汽车的交易额超过2万亿,初步估计每年的绿色信用现货市场规模保守在百亿以上,期货市场规模至少在千亿级别,预计每年可为这些城市节约能源1亿吨标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
绿色秩序的制度设计使得市场与民众将有可能为城市生态治理带来新的变革性的推动力。这样的大众参与本身即是一种绿色力量的教育和传播,将有可能带来乘数级的效果。尽快开启超大城市生态治理的大众模式,让“微生态”成为社会新风尚。
作者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