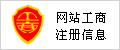前 言
近一年多来,我就燃煤发电超低排放发表过多篇文章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讨论。其中,《中国能源报》曾在报道中针对“近零排放”引用了某集团公司领导的话:“不管烧什么(燃料),关键看排什么(污染物)、排多少,只要排放合格就没有问题。”又说“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写了文章质疑我们,我们不去争论,只以环保效果和实际效果去验证,到底从经济上、技术上是否可行,由时间来评判。”
我赞同这些话,因为它基本概括了燃煤电厂为什么选择超低排放(或者“近零排放”),以及超低排放需要深入思考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包括用什么标准评判污染物排放是否“合格”,用什么样的方法验证设备的超低排放“效果”,用多长的环保设备连续运行时间来判别超低排放技术是否“成功”,如何判别超低排放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是显著还是微不足道,用什么指标来评判技术与经济“可行”等。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对超低排放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一项体育运动,如果连规则都不明确就来谈比赛的胜负是没有意义的一样。
因此,对于推进超低排放,我认为我们缺少一个评判的规则,其次是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本期中国环境报《声音》版上,我想先就如何建立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科学评判体系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要评判一项政策或行动的效果之前,首先要明确组成这个政策或行动中关键要素的内涵,否则就可能形成“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本文所指的“超低排放”概念为:在烟气中的氧含量折算为6%的条件下,燃煤锅炉排放烟气中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3项污染物的浓度小于或者等于5(或者10)mg/m3、35 mg/m3、50mg/m3的排放行为。相应地把标准中燃煤锅炉执行小于或者等于20 mg/m3、50 mg/m3、100 mg/m3特别排放限值的排放行为作为与超低排放进行分析比较的参照。
立足于全社会的利益、环境质量改善的本质要求以及科学推进超低排放的角度,我认为,超低排放的评判体系应由指标体系、价值体系、方法体系、推进体系等4个方面构成。
四体系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指标体系,即能够全面、简要、准确、方便反映超低排放的目的及主要特征指标,指标间应互相独立并从不同侧面反映超低排放的本质属性。比如在反映超低排放的效果时,是用污染物的削减率还是用环境质量的改善率。
价值体系就是要针对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寻求优、良、中、差的价值判断的分数线。比如,超低排放每千瓦时电量需要增加一分钱,这一分钱成本是合算还是不合算。
方法体系就是描述评价指标的数据,是在什么情景下、条件下,由什么人(或者组织),用什么方法得到的。比如排放效果的数值是否由真正意义的第三方用合适的、规范性方法进行监测所获得。
推进体系就是对企业“超低排放”的普遍性要求由谁来推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需要什么样的政策配套等。比如是通过出台文件推进还是通过修订排放标准来推进,还是与企业签订自愿协议推进等。
从4个方面的内容和作用容易分析出:指标体系是基石,价值体系是灵魂,方法体系是关键,推进体系是保障,而且形成了递进式互相依存的关系,缺少其中的一个方面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存在的价值和作用的发挥。
构建好以上4个方面的体系,我们就可以对超低排放的效果进行清晰而全面的评判了。近年来,对超低排放的具体项目和普遍性进行的种种评论或者评价,并不是用一个公认的评判规则进行评价的,以偏概全,或者以普遍性否认特殊性的情况都是存在的。
指标体系:选择反映本质属性的指标,避免选择表面化的指标
超低排放要求针对的是具体的排放对象,如锅炉排放、燃机排放等,从要求的性质看属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范畴,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体现排放标准制定的基本要素。
我国《环保法》对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原则要求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基本相同,主要涉及3个方面,即环境质量要求、经济代价、技术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重点是选择反映本质属性的指标,避免选择表面化的指标。
由于超低排放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环保,针对我国目前大气环境污染的最主要特征是雾霾污染,如当前采取的对燃煤总量的限制和煤电发展的限制,都是以治理雾霾污染为动力的,因此,必须要明晰煤电超低排放对减轻雾霾的作用。在具体指标的选择上应考虑3个方面:
一是要选择环境质量改善的指标。表达环保效果的指标有煤炭总量减少量、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达标排放率、单位国土面积上的减排量等,由于环境质量改善不仅与排放量减少有关,而且与地形、气象等条件有关,指标选择最能够直接反映对雾霾影响的是电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空气中的PM2.5浓度的影响大小。
二是选择可比较的污染物减排边际效应指标。由于定量考虑边际环境效益难度很大,具体操作中可以定性考虑。
三是由于雾霾的影响是多种污染源和污染物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将燃煤电厂的排放影响与燃煤散烧及其他污染源的排放影响的分担率进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经济代价指标与技术水平指标,主要是分析在环境目标下的经济可行性与技术可行性问题,也是支撑环境指标的基石,脱离了经济代价与技术水平下的单纯环境指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选择上也应考虑3个方面,一是统筹规划,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看,考虑是把全社会有限的财力和技术用到燃煤电厂“锦上添花”还是在别的领域“雪中送炭”。显然,经济、技术指标应当兼顾到对整体性和全局性决策有重要参考作用。二是经济、技术指标包括的内容很多,在选择上也应体现关键性指标,同边际环境效益指标的作用相同,边际污染物减排经济代价更具有实际意义,如超低排放时,烟尘的边际污染控制成本可能会大于全社会边际污染控制成本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三是要考虑到电力生产安全性、可靠性、持续性、响应负荷变动的特性。
价值体系:采用最佳可行技术(BAT)原则
价值体系是针对确定的指标给出优、良、中、差的评分标准,以进一步确定达到什么级别对应什么样的推进范围、程度和速度。评分标准最好是定量,也可以是定性。正如高考的分数线在全国也不一样,同样,对超低排放的要求和代价是否合理,在全国也不一样,是与各地的经济、环境、技术水平密切相关的,如对于某一个地区电价增加3分钱也可承受,而在另一个地区电价不增也难以承受。超低排放的水平全国也应有所区别,绝不能“一刀切”。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可以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已经确立的燃煤电厂采用的最佳可行技术(BAT)原则。
根据BAT原则,应当由政府部门制订出一个分数线,作为价值评判的依据,即符合最佳可行技术原则为“优”的原则。
对于BAT原则立足点不同,结果也会不同,从政府推进角度来看,应当从全社会层面来衡量电厂超低排放的价值。企业根据各自的战略主动推进超低排放,虽然无可非议,甚至予以鼓励,但是某一企业的意愿并并不等于社会层面的可行。
比如在某一地区,企业愿意每千瓦时增加两分钱甚至更高成本实施煤电超低排放,是因为这样做要比政府同意企业采用天然气发电成本(比煤电高出2~3角钱)要低90%以上。但是,政府应当考虑,如果将天然气用于民用替代散烧煤要比用于发电有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只要燃煤电厂达标排放,是不会污染环境的。天然气发电价格太高当前只适用于调峰,不适用于替代基本发电负荷,要求企业以气电代煤电本来就不是合适的政策,让电厂超低排放从全社会看其投入和产出的环境效益并不一定合算。
方法体系:关键解决技术规范和评判机构问题
在方法体系的构建上关键是要解决好用什么样的技术规范和什么机构来评判的问题。
从目的性来看,将超低排放的要求修改到排放标准之中与工业项目的科研验收以及技术普遍适用性验收采用的评判方法显然应不同。
对于一个具体项目,可以参照环境保护部《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管理办法》(环发〔2009〕58 号文)中的一些原则。如遵循客观、科学、公正、独立的原则,采取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专业评价人员与技术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当根据评价指南、规范等技术文件开展评价工作,评价结论应当明确被评价技术的可行性、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可达到的环境、技术和经济指标,以及存在的技术风险,不得滥用“国内先进”、“国内首创”、“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填补空白”等抽象用语等。但是对于大面积推进的超低排放,则应当采取根据BAT原则修订排放标准的方法进行评判。
美国、欧盟制定BAT参考文件对每个行业来说制定时间平均耗时3年~5年,而我国2014年的煤电排放限值要求一年内就变化了3次~4次。
推进体系:“说法”期望得到法定标准确认
如果按照上述几个体系的要求开展评判,并最终将 “超低”纳入排放标准的要求,“超低”也就成了 “普通”或者是新的“特别排放限值”。
从这个意义讲,“超低”确认过程以及未进入排放标准之前,只是一种“说法”,或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定要求。
我国是法治国家且“依法治国”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持续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既与广大人民的环境利益有关,也与千千万万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关,归根到底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关。
所以,推进超低排放,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企业进行合法性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