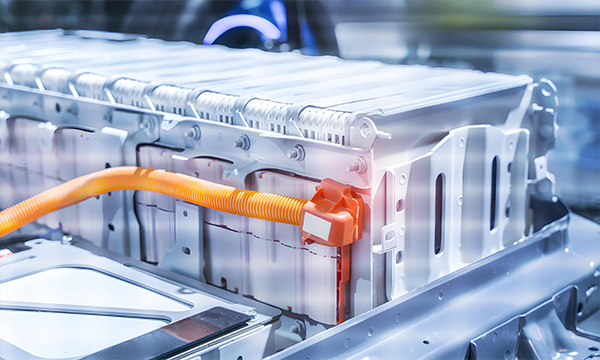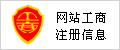从技术特点看,风电与光伏都具有通过研发、技术外溢以及干中学取得成本下降的潜力。推动市场规模也可以激发成本下降式的创新。但在初期成本高昂的阶段,没有足够市场容量,成本下降的过程就不会启动。
也就是说,风电具有成本下降的潜力,但这种潜力的释放需要借助额外政策。优惠电价作为一种补贴,是提高风电市场份额的主要政策工具。
2014年风电装机接近破亿千瓦,在全国来风情况普遍偏小的背景下,平均利用小时数1893小时,弃风率8%。面对火电利用小时还高达4000小时的现实,可以说,即使现有的电力系统完全不变,风电并网的技术潜力仍远未实现。2015年初,风电标杆优惠电价有所下调,电力体制改革业已开始,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帐户仍然吃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对风电意味着什么?
可再生能源需要支持是因为清洁无污染吗?如果是这样,为何不给水电优惠电价呢?
风电清洁并不构成需要优惠电价的理由。因为,第一,如果清洁意味着价值,那么风电的这种优惠电价(大约比传统煤电高0.25元),其确立的依据就应该在于这种减排污染的效应有多大,从而让其能够跟传统发电技术在同一环境下公平竞争。这类似于法律意义上的“刑罚适当”。但优惠电价水平的确立显然不是以反映清洁的价值为目标的,而是以可以使风电正常盈利为目标。
第二,以这种方式减排的成本很高。优惠电价固然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对降低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吸引力没有任何帮助。同时,由于这种补贴将降低电力的整体电价水平,从而引发需求反弹,减排将更困难。
从技术特点看,风电与光伏都具有通过研发、技术外溢以及干中学取得成本下降的潜力,前二者可以归类到技术创新的推动,而最后者可以归为市场的拉动。推动市场规模也可以激发成本下降式的创新。但在初期成本高昂的阶段,没有足够市场容量,成本下降的过程就不会启动,很难形成足够的、有市场竞争力的规模。
也就是说,风电具有成本下降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的释放需要借助额外政策。优惠电价作为一种补贴,是提高风电市场份额的主要政策工具。
2014年,风电业界出现了一种担忧,认为电力市场化改革会危及风电的支持政策。这是不必要的担忧,混淆了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
各种发电机组一旦建成,其投资成本,以及固定的运行成本(比如还贷、人员工资)将成为“沉没成本”,系统要成本最优化,必须首先使用那些可变成本低的发电类型。可再生能源没有燃料成本,自然是最优先的选择。只有这样,从“做大蛋糕”——系统最优化的角度,也才是合理的。因此,在我国存在的火电与风电争发电小时数的问题,首先应该描述为一个整体系统最优价值标准下的效率问题,而不是一个风电与火电分蛋糕的“利益分割”问题与视角。历史存在的利益格局,比如行政定立的平均发电小时数,不应成为打破这种格局的政策障碍。
这也是为什么现货电力市场,其定价体系基本都是基于边际成本设计。在一个边际成本决定价格的电力市场中,低边际成本将无限压低市场整体的价格水平。众多文献的检验表明,在西欧目前的电源结构下,可再生能源每增加100万千瓦,市场的价格水平可能就要跌落6-10欧元。
当然,长期而言,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到底会提高还是降低电价是一个很有争议、甚至很难定义清楚的问题。这些影响,在我国高度管制的电力系统中,尚未充分暴露。
在政府文件中,出现了“风电到2020年价格与火电持平”的预期性目标,但如何操作仍不得而知。
就笔者的观点而言,这种僵直的目标是需要取消的,不应简单作为取消补贴的时间表。面对技术进步与市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火电负外部性内部化的程度,这种目标缺乏一定的弹性。并且,政府已经设定了风电2020年实现2亿千瓦装机的目标,如果实现了风火同价已经可以分散决策,自主发展,何需此种装机目标?装机目标与价格目标,只能存在一个,或建立二者之间的定量联系。
从地区角度来看,中国、印度等具有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寄希望于别国成本下降之后技术输入是不现实的——发达国家各种要素成本高,不发达国家缺乏制造业的基本能力,成本更高(比如非洲)。唯一期望的就是自己通过实际规模扩张,技术学习以降低成本。15年左右的风电支持期(从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出台算起),无论从国际同行经验还是技术进步的节奏来看,都显得有些过于仓促。
(张树伟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陈东娟供职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