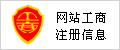在环境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区分“人为的”产权界定和“作为企业家行动之结果”的产权界定,不要把两者混淆在一起。
许多受张五常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倾向于把“产权界定”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譬如,为解决甲地的雾霾问题,把排污权界定给乙地的钢铁企业,这样一来,只要甲地居民“踊跃地掏钱”给乙地的钢铁企业,补偿这些企业因少排污、不排污而受到的损失,似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种用“人为界定产权”的方法来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恰恰忽视了科斯的“交易费用”问题,它把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无论何种产权安排效果都一样的思路“套用”到了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中来。
这种“人为界定产权”的方法预设了某种产权安排可以改善社会福利,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把产权界定给乙地的钢铁企业,然而,这个结论却是武断的:他如何知道产权这么界定而非那么界定就一定可以改善福利了呢?这种方法所隐含的前提是界定者已经知道所有个体对环境的评价和支付,从而可以给出一个最优的产权安排,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理性的狂妄”而已。
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看,既没有客观的环境问题,也没有客观的环境成本。不同的行为个体对他的处境会有不同的判断,会采取他认为成本最低的方式来改善他的处境。因此,并不是政府把污染水平降低了,就意味着提高了社会福利,而是要让每个人、每个企业家都能通过价格信号,对他的处境、他所感知的利润机会作出反应,使他们能够有机会采取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手段来改善境遇。在这个过程中,产权会由于企业家的上述行动而不断地被调整,产权的调整过程,也是他们对“他们所认为的问题”的解决过程。由此可见,产权的调整一定是以“分散”的方式进行的,并且也总是一个“过程”,而并非如人为界定产权的方法那样是“一劳永逸”的,后者在方法论上预设了某种最优:即他已经知道“污染”产生的社会成本,从而认为通过他设想的“界定产权”的方法能最优地解决这个问题。
个体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打算消除他所受到的环境影响(负外部性),因为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成本可能很高,并不值得。同一种环境影响,在不同个体的价值序列中的位置不同,即对不同主体而言,“成本”并不同,对有的个体来说,消除某种环境影响非常迫切,但对另外一些个体来说,消除那种环境影响就不那么迫切,譬如对住在马路边的个体来说,有的会把解决噪音困扰摆在优先解决的位置,有的却不会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可以把解决噪音的资金用于满足效用更大的目的,消除那种环境影响对他来说反倒是得不偿失。一般来说,环境影响已经体现在价格中,如美丽的湖边,住房价格往往很高,而嘈杂的马路边的房子价格往往比较低。这时,环境影响已经作为一种成本,进入到个体的主观评价中,比如他在购房时,会权衡房价与包括环境影响在内的各种收益与成本,判断某一价格是否划算;假如政府在他购房之后消除了马路的噪音,那就相当于给他提供了补贴,因为这样一来房价就会上涨。
哈耶克认为“产权”是解决纠纷的办法,产权如果不清楚,那么就会出现公地的悲剧,如雾霾等,因此,产权需要明晰、需要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产权”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是指对“物”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更是强调如何“发挥人的才能去解决问题”,而人们通常意识到的往往只是前面的这层含义,认为只要把水或土地等资源的产权界定弄清楚了,环境问题似乎就解决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允许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物”的产权界定只不过是人们作为企业家发挥其才能的结果。
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的调整必然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种产权安排是“最优的”。作为企业家行动的结果,原来的产权结构会被打破,新的产权会被建立起来,此番产权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环境改善的过程,政府不应该人为地限制产权的调整,比如把某些资源定为“公地”,阻碍人们在这些领域建立产权,这将会阻碍环境的改善。
所以,在环境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区分“人为的”产权界定和“作为企业家行动之结果”的产权界定,不要把两者混淆在一起,错误地认为“人为的”产权界定也是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