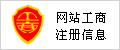空气质量改善与污染物总量控制,是大气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空气质量改善是目的、是结果,污染物总量控制是途径、是手段。但是,在大气环保具体工作中,二者关系经常错位。
这种错位体现在哪里呢?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及污染治理任务通常是明确的、具体的,且可按行政区进行分配或下达;而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却涉及产业与能源结构、污染源的空间分布、气候与气象等因素,而且不同大气污染类型的空间尺度相差很大,如灰霾污染往往是大尺度范围的,由于污染企业无组织排放导致的恶臭污染往往是小尺度范围的。
应该说,过去的大气环境保护是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的。但是,在家底不清、监测体系不完善、监测数据真实性受置疑的情况下,过于倚重总量控制,难免出现总量控制指标连年下降,空气质量仍持续恶化的尴尬局面。
当然,APEC蓝似乎让这种尴尬看见了一线光明。我们不妨将北京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方案,视为一次积极且效果不错的“地方试验”。姑且不论成本,单从效果看,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目的。类似试验在此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及2014年南京青奥会期间多次进行,效果无一例外,还不错。尤其是2010年长达6个月之久的上海世博会空气质量保障“试验”,可称得上是场“中试”,甚至是“小试牛刀”。
这些试验从数天到数个月、从北方到江南华南、从夏季秋季再到冬季、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单打独斗再到多个城市和地区的联防联控,类型越来越多样,经验越来越丰富。从小处讲,有益于提高未来重污染天气防控对策的科学性、对策作用点的精确性以及防控成本的有效性;从大处看,是中国探索从“世博蓝”到“APEC蓝”、再到“常态蓝”,改善空气质量的良好开端。
试验之后,我们应认真编制“试验报告”。报告内容除了通常应包括的,如试验期间防控区域内所有监测点站的空气质量情况、同时期气象条件、每次试验的空间范围、防控对象(如重点企业、建筑工地、机动车出行等)及防控程度等以外,还应有一项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防控方案的实施成本或代价,特别是成本该如何分担。
成本或代价如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和社会之间分担?这关系到能否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形成改善环境质量的合力,也是建立改善空气质量乃至整体环境质量的根本措施和长效机制的关键。无疑,这还得依赖制度。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不仅仅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相关领导的口头上,而且已经落实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治污的行动上。作为环境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尤其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法律与政策、群众的权益与责任四方面关系。
首先,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与分工。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新《环境保护法》也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正在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空气质量”与“污染物总量”的关系上,应构建“双约束”格局,即本级人大监督地方环境质量目标达标情况,上级考核下级总量控制任务完成情况。也就是说,由本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本市政府环境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明确县级以上行政区(省长、市长、县长)需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包括大气环境在内的环境质量状况、环境质量目标实现情况、污染治理目标完成情况等。
另一方面,也应考虑空气及大气污染的流动性和区域性特征,及控制、治理的适宜空间尺度,将大气环境质量目标实现情况和大气污染源治理、监督等情况分开。比如,作为污染治理的污染物总量控制、重大污染源的监管、污染事故事件的处理处置等,应强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尤其应着重各级行政区内完成大气污染治理任务的协调,形成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合力。
而国家层面,应侧重于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立法、制度供给,以及跨省级行政区大气污染治理的协调和全国范围的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在污染源监管和污染物总量控制上,应在增强县级环境监测与管理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属地管理,改变地方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央企的现状。
其次,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还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或家庭,都应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这也是“污染者责任”原则的体现。污染者很难自觉履行其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强制性及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政府又不宜直接干预污染者这一微观主体履行其责任的方式和手段。因此,政府不宜强调,对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产品、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实行淘汰,而应通过制度设计,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严格执法,倒逼排污者改善排污行为即可。
正在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应限定能源类型(如煤炭)和供热方式(如集中供热),而应强化污染源监督,督促各地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目标。至于选择什么供热方式,由各地和市场自行选择。
再次,是立法的公平性与政策的针对性。
总量控制作为特定政策,基于效率性原则,政策性、针对性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在中国环境保护起步阶段。但是,总量控制如果一味地强调针对所谓重点污染源、重点污染物,就隐含了坐等“小污染”变成“大问题”才采取行动的意味,这显然与污染治理中“预防为主”的原则相悖。
环境管理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严,而在公平(污染源无论大小)。我认为,本次立法应明确或强化公平性、普遍性。也就是说,总量控制应针对所有区域(无论所谓的重点区域还是一般区域),所有污染类型(无论工业源还是生活源)、污染源(无论大小)、污染物种类。
当然,总量控制的针对性依然重要,只是应强调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分类指导(比如大气污染较重的城市、较好的城市等)。在明确总量控制与质量达标之间的关系,或关联性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对总量控制指标完成与否、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与否、污染物排放标准达标与否,分为不同类型区域或城市,提出针对性的要求。
最后,公众参与的权益与责任。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包括普通公众、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政府、企业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尤其是应以制度保障公众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和企业排污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本着“污染者责任原则”,进一步明确公众作为污染者(即日常活动如衣食住行等的污染行为)的责任和义务。
总体来说,我认为,应根据不同大气污染类型及与之相应的、适宜的空间范围,先制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再制定各类污染治理及总量控制的要求,最后再按行政区和行政层级落实其产业与能源升级、污染源治理的任务。解决好空气质量改善和污染物总量控制这一核心问题,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APEC蓝才有望成为常态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