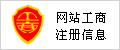2014年12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国务院向全国人大首次提交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于1987年,并于1995年、2000年先后做过两次修改,距今已近14年未做修改,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不仅关系到何时能够重现蓝天,而且与每一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根据中国的修法惯例,一部法律修订草案,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审议才能进行表决。为此,就《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该如何更好地修改,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
应进一步加强与新《环保法》的衔接
记者:您如何整体评价《修订草案》?
王毅:本次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跟前一段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的稿子变化并不大,我同一些从事环境保护的专家学者进行过一些讨论交流,大家普遍认为,目前《修订草案》跟我们实现防治大气污染和“重现蓝天”的目标要求还有比较大的距离。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比较大的差距?
王毅: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它没有全面落实新《环保法》的各项规定,其中很多的条款基本都是简单的重复,没有突破,包括像区域联防联控、按日连续处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而新《环保法》的原则只有在单行法修订草案中得以落实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二是作为单行法,如果规定过于原则,则与我们目前所处的严重大气污染防治阶段的要求不符,特别是其中一些程序性、时限性的规定更加缺乏。由于过于原则的规定,也给执行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和过大的行政管制空间。
最近焦点访谈报道的山东鲁抗医药股份公司偷排含有大量抗生素的污水案例,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情况,含有抗生素的污水污染之前也有过报道。但这次事件透露出的是,排污企业、第三方运营单位以及地方监管机构出现了系统性的漏洞,不是某一个部门出了问题,而是从数据到监管整个链条都存在问题,同时也给现在要推行的“第三方治理”敲响了警钟。
三是目前的修订草案主要还是以末端治理为主,没有更多考虑关口前移,或者说部门立法的痕迹还是非常明显,没有统筹考虑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多元共治,特别是多部门、多地区、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应作出一定突破
记者: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能严格修订,三中全会提出的“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就无法落到实处。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模式您有何建议?
王毅:建议人大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为契机,更多地考虑在立法模式和立法思路上进行改变,转变部门立法的模式,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吸收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法》跟民生联系非常紧密,又是涉及到社会经济多个领域和多部门的管理事务。
改变立法模式,更好地发挥人大的作用,不仅有利于落实人大常委会2014年4月份通过的新《环保法》的各项原则,而且还会为之后将要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提供一个好的案例;否则,沿袭目前这种修改力度和模式,有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同时,建议把目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清洁空气法》,这不仅是字面上的修改,而是从被动的污染防治转变为主动地提供清洁空气、提升环境质量,这与当前发展经济和消除严重灰霾天气的双重目标相一致。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治污的思路也是从末端治理向前端转移,是从治理思路上、方式上、立法手段上的整体转变,同时把立法、执法、和司法统一起来。因此,我们要打破部门立法框子,从转变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全方面控制灰霾产生;如果仅从末端治理,我们“重现蓝天”的时间就会往后拖。所以要考虑从更广阔的角度研究清洁空气提供,而不是仅考虑末端治理。
同样,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有关清洁空气的立法越来越精细化。例如这次《修订草案》条文是100条,约21000字;再看美国的《清洁空气法》,1990年设立,经过多次修改,目前翻译成中文大概有60万字,是我们现在的30倍,虽然它只有271条,但每个条下有子条,子条下有款,对各项措施都有非常严格和精细的规定。
当然美国的模式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把各类标准、措施、程序性规定等都统一在一起,所有防治措施都能找到相应条款。再比如在南加州,污染罚款从1000美元到100万美元,每一档都有明确的说明,包括附带刑事责任,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小,这才叫精细化管理。我们现在的环境保护离精细化管理还相差非常远,因此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制定“中国版”的清洁空气法。
记者:《修订草案》是否应该提出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时间表?
王毅: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应该有明确的程序性和时限性规定,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国现在提出到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2025年前后煤炭消费总量也可能达峰。那么,我国的空气质量是否也可以提出到2030年左右使主要城市和三大重要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实现二级标准。
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要求法律的精细化制度安排须实行分区域对策。可以根据质量标准达标情况,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等手段,给予不同地区差异化制度安排,应对减排目标做出刚性的、程序性的规定。针对具体污染物来讲,我们过去只有两种大气污染约束性指标,而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列出的标准污染物和有害污染物将近200种。虽然我们不一定将这些污染物都列出来,但最起码要针对最主要的5-10种污染物制定详细的减排制度措施,包括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
记者:《修订草案》对大气污染的区域性特点也未提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此,您有何建议?
王毅:目前,关于区域联防联控在《修订草案》里规定得比较空泛,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在国际上已有比较好的经验,比如美国有联邦环保局派出的大区机构。
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虽然现在要进行环境大部制改革还存在一定困难,为什么我们在区域污染控制上不能寻找突破口,尝试设立一些区域(包括流域)的环保派出机构,建立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统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通过这样的制度创新,才能使所谓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通过试点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常态化限行值得商榷
记者:《修订草案》没有关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内容,对此,您怎样理解?
王毅:关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问题,在新《环保法》中都有专章表述,这也被认为是新《环保法》的一大亮点。但在与公众息息相关的《修订草案》中,关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的内容很珍惜笔墨,没有更详细的制度规定。
我们知道,设置再多的政府管理人员也不可能代替公众参与,只有当地的老百姓才更了解实际情况,更了解当地的排污企业,也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更好的监督,所以我们可以设立更好的制度,增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化程度,鼓励有序公众参与,包括奖励举报、惩罚造假,发动公众发现和制止企业污染行为。
同时,还要加强按日连续计罚的力度,加大执法,否则我们所谓的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局面就难以改变。除此之外,《修订草案》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希望能够更多征求利益相关方的观点,不要急于尽快通过,而是进行科学细致的修改工作,使修改质量不断提升。
记者:《修订草案》提出在重污染天气下地方政府有临时限制车辆运行的权力,但也提出来可以常态化的限制车辆使用。对此,您如何评价?
王毅:常态化限行制度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不应给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行政性限行或禁行留下空间。北京市的车辆限行规定恰恰提供了一个负面的案例,过去本来限号行驶是一个临时行为,但其结果之一是加速了北京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很多家庭都有了两辆车,也没有因此获得补偿,现在又在讨论单双号运行的可行性,似乎要将这种行政性限行常态化。
虽然限行和禁行有不同的方案,但我个人认为,以损害私人财产利益为基础的常态化行政性限行是不良条款,不仅无助法控制汽车数量的增长,也无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这已经被许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因此,这类条款不应列入到《修订草案》。
实际上,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讨论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就提出“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构建公交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把更多的路权给予公交,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采取市场化手段调节出行方式等。
总之,我们还需要做更细致的修改,使大气污染防治法或清洁空气法能成为改善大气质量的制度标杆,真正实现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