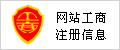APEC会议期间,中国首次正式提出在2030年左右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即在2030年之后碳排放不再增加,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一次能源是指直接取自自然界、没有经过加工转换的各种能量和资源)。而舆论普遍关心的是时间表确定了,那么水平呢?事实上要解读峰值时间和水平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对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探讨,要判断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是否有条件科学、公平、有效地达到排放峰值。为此,工业化、城镇化、能源消费、区域发展这四方面是需要重点分析的内容。
工业部门的排放峰值
工业化过程是排放峰值是否能够尽早达到的首要因素。工业部门排放约占当前排放总量的70%,即使不包含工业过程中的排放也已超过51亿吨二氧化碳。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分别已经达到60%或66%(不同指标),中国整体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一般认为,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水平大约在80%以上,也就是说还有近20个百分点的空间。从工业化国家和中国历史数据比较来看,工业化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则相应增加约0.6亿吨,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时工业部门至少还要增加约10-12亿吨排放,总量将可能超过61亿吨。工业化水平超过80%以后,即工业化后期的下半阶段,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增长主要在新兴和服务产业,相应1个百分点平均降为约0.3亿吨,即意味还有6亿吨左右的增量。那么当前至2030年工业部门排放总的增量在16亿吨左右,排放峰值大约为67亿吨。
根据行业协会对目前主要11个行业产品产量趋势的预测,合成氨峰值约在2015年,水泥峰值大概在2017年(约26亿吨),粗钢峰值可能要到2020年(约8.5亿吨),平板玻璃和电解铝峰值估计在2025年,都要比原先预判的延后。主要高耗能产品排放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虽然是可以争取的,但从预测的峰值水平来看,要高于之前估计的数值约20%-30%。而高耗能产品产量趋稳后,工业部门排放仍将缓慢上升5-10年的时间,因此2025年前工业部门总体达到峰值有难度。
城镇化排放的峰值
城市将是中国未来排放的主要增长来源。交通和建筑等部门当前占排放总量的近30%,已超过21亿吨。中国正处于工业经济为主向城镇经济为主转变的阶段,城市化仅为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同等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未来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般的城镇化过程在20%-30%的水平起飞,越过50%以后会放缓。城镇化趋于平稳和终结时点可参考:一类是移民国家,一般到80%-90%,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另一类是原住民国家,一般到65%-70%,比如日本、欧盟部分国家。中国2012年的城镇化水平约为52.6%(按照户籍人口测算仅为35%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国内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总体可达68%-72%的水平,还有近20个百分点的空间。考虑到后期速度的放缓,存量的深度城镇化(“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超过2亿人口)和增量的城镇化(约3-4亿人口)至少仍需要25-30年的时间。按OECD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能耗和排放大致是城市的3倍,而中国的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约1.5倍、城镇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农村地区的约4.5倍,相应的总能耗和排放约为农村水平的3倍。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格局的变化对排放峰值水平影响很大,而城镇化过程中建筑和交通模式一旦形成和固化,能耗和排放是较难降低的。
中国当前的城镇化速度是每年约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新增建筑面积近20亿平方米、机动车近2000万辆。从发达国家和中国历史数据比较,城市化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交通和建筑等部门新增能源需求约800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将相应增加约2亿吨,意味着在工业部门排放增长之外,中国完成增量城镇化过程还可能至少增加约40亿吨排放,完成存量的深度城镇化预估也要增加约17亿吨,总量将可能达到78亿吨。也就是说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排放总量峰值可能达到约145亿吨(仅包括能源活动排放),即使不考虑存量问题也至少要达到128亿吨,未来25年的平均年增长量至少约为2-3亿吨(约为当前年增长量的一半)。因此,在2030年前要实现排放峰值仍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峰值水平要显著高于110亿吨。如果按110亿吨目标实行倒逼机制则意味着在产业结构调整假设的基础上还要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减少年排放量至少20-30亿吨。
能源结构调整的潜力
能源结构调整将对峰值目标的实现起到决定性作用。据统计,非化石能源2012年的消费量约为3.3亿吨标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9.2%,煤炭约占66.4%,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约占18.9%和5.5%。当前能源结构高碳特征明显,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能源结构清洁化和低碳化的空间至少有20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同等消费总量下可以减排10%-25%左右,问题是可行的调整速度是否能够满足峰值目标要求。事实上,过去20年中能源结构调整幅度非常有限,非化石能源比重仅上升3.5个百分点,煤炭比重下降8.2个百分点,石油比重上升2.4个百分点,天然气比重上升2.3个百分点。即使自2005年加强政策力度以来,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的速率快了一倍,每年也仅略高0.3个百分点。
如果至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速度相比于“十一五”时期再提高一倍,即每年0.7个百分点左右,则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将接近1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超过30%;而2020年至2030年继续保持相当速度,即每年0.5至1个百分点左右,则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到20%-2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超过45%,与此同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煤以内,煤炭占比降低至45%左右,天然气占比增加至10%左右,那么能源活动排放大致可以控制在110亿吨左右。但那就意味着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量要翻一番,达到7亿吨标煤以上,非化石电力装机要超过6亿千瓦,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量要再翻一番,达到15亿吨标煤以上,非化石电力装机要超过10亿千瓦。这种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美欧,是极为罕见的,从以往的经验数据看,相当于年投资额要超过1万亿元。而同时天然气的消费量要达到4000亿立方米,如果新增量的一半来自于页岩气开采,那么需要打3万口生产井以上,总投资额也将接近于4万亿元。结构调整速度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代价都很大。
事实上,如果按照上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能源消费总量大致还要增加30亿吨标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加速发展也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增量需求。“十二五”煤炭消费量规划已为39亿吨,即使2030年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下降至45%以下,即今后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煤炭消费总量预期仍会大大突破40亿吨,增长至45-50亿吨,并将长期处于该高位平台区间。
全国“同步低碳”的区域差异
区域发展差异性将对峰值目标部署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区域在发展水平、功能和结构上非常不平衡,事实上从多类研究指标标定的发展阶段看,中国区域间发展梯度可能长达20年甚至更久。目前东部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其中东部两个直辖市已跨入后工业化阶段,中部和西部则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中西部5个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两个自治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对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规律认识,促使我们更为理性地思考全国“同步低碳”是否可行的问题。事实上,虽然东、中、西部2011年的人均GDP还存在较大差距,分别约为4.4万元、2.5万元和2.3万元,但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已达到约3.4吨标煤、2.9吨标煤和3.0吨标煤,人均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也已达到约7.9吨、7.0吨和7.7吨,已相对较为接近。
从工业化过程看,东、中、西部2011年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分别约为81%、59%和51%,“十一五”期间年增长率平均约为5.4、4.2和4.8个百分点,按照历史和规划数据预测,东、中、西部基本完成工业化分别约在2011年、2021年和2023年,完成全阶段工业化过程分别约在2018年、2031年和2031年,东、中、西部工业化过程排放到达峰值前的增量还有约2亿吨、6亿吨和8亿吨;从城镇化过程来看,东、中、西部2011年城镇化率分别约为61%、47%和43%,“十一五”期间年增长率平均分别约为0.9、1.2和1.4个百分点,按照历史和规划数据预测,东、中、西部基本达到约70%水平分别在2024年、2034年和2036年左右,东、中、西部城镇化过程排放到达峰值前的增量保守预计约为9亿吨、16亿吨和15亿吨。
应该说,中国区域的梯度特性既为中国长期发展创造了波浪式的后劲和潜力,同时也延长了增长的过程,意味着全国的排放峰值将取决于区域间发展的叠加效应,峰值前后的平台期预计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当中,东部确实应率先控制排放,但如果中西部不达到峰值,全国排放峰值也很难实现。因此,国内各区域的减排政策应在公平和差异化的基础上同步推进。
实现战略目标的建议
中国的排放峰值和发展方式息息相关,需要统合起来全盘考虑,科学、公平、有效的峰值目标将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但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峰值方案的风险和挑战性。
中国总体上还存在20%的工业化、20%的城镇化、20%的能源结构调整、20年的发展跨距要面对,应该有步骤地实现排放趋稳,并在更大的社会经济全局内权衡,阶段性的排放峰值目标决策方式和渐进式的峰值目标计划有助于凝聚共识和降低风险。
同步推进针对工业化后期的生产性排放增长和城镇化后期的消费性排放增长的控制政策目标和手段,重视部署后发展地区的“同步低碳”战略,确立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碳功能定位,形成公平的区域差异化气候政策体系,有序建立行业碳排放标准准入和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与市场机制等关键制度。
深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排放控制应该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央地财权事权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等结合起来,将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纳入政绩考核,给予地方政策创新和改革试验的灵活性和差异化评价,有效形成中央和地方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是中国计划和实现排放峰值的出发点和最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