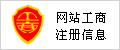那应该是2002年,水利部的官员对我说,你应该到紫坪铺和都江堰看一看,那是四川社会经济以及整个中华水利文明的两个亮点—它们相距仅9公里,时差却足足有2256年。紫坪铺水利枢纽是国家西部开发“十大工程”之一,四川的“一号工程”,号称“成都三峡”;而位于其下游的都江堰则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绵历两千多年“不废不衰”,无坝分流,天人合一,是不折不扣的千古奇迹。中国历史上两大水利巨制在岷江上游穿越时空唇齿相依,“治水兴蜀”之理想似乎水到渠成。
但紫坪铺与都江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水思想的产物,围绕紫坪铺的上马出现了激烈争论。我去紫坪铺几次,也写过一些报道,在汶川大地震中,这座摇晃的超级大坝着实让我们捏了一把汗。不过,我们暂且抛开工程优劣利弊之争不谈,只在这两个相距两千多年的“亮点”之间划一条连线,我们就会感觉到,这条连线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社会组织机制的演进脉络。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便进入了一种由亚细亚灌溉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并产生出一整套的“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与大河流域生产关系密切相关。此说未必全对,但有助于启发我们的思考。其实,我们自己更熟悉“治水如治国”的古训。两千多年来,治水对于我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的政治问题,带有深刻的传统文化制度烙印。我们看到了这种传统社会组织模式集中国力办大事的效力,但是—从都江堰到紫坪铺—传统水利社会的文化也面临着现代社会思想的冲击与嫁接。
“魏特夫理论”认为,水旱无常的地方往往成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国北方、印加帝国等。在这些地方,水资源必须加以管理、开发与分配,必须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就需要动员和征召人民,并需要一个强大的公共管理中心来管制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水利系统。当淡水成为稀缺资源,更要仰赖中央集权管理的水利系统,于是就会出现具有成熟控制体系的高度发展的水利社会。那时候,国家机器是否能够长治久安,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处理包括水旱灾害在内的社会危机,灌溉农业系统的运作极大地影响到集权帝国的建立与稳定。
据说,这种管制色彩浓厚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许多国家。比如美国的田纳西谷地管理局,从1930年代开始,就把中央集权与官僚化的水资源管理模式结合到流域发展计划,以此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1950年代,美国的另外一些州政府和全世界众多国家都广泛采取了这样的水资源管理模式。
于是有人就说,从长远看,人口在不断增加,淡水将成为绝对的稀缺资源,只有这种官方集权式的水利行政系统才能有效控制与分配水资源,并使水利系统正常运作,进而保障国泰民安。但是且慢—由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出现飞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关系更加复杂,那种传统的水利社会的生产关系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要与时俱进地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让传统水利社会的遗产更加有效地服务现代社会。
中国数千年的水利文明实际上是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结晶,都江堰工程就是一个集大成者。它留给我们的本来是一种宝贵的系统思想,但我们没有发展这种思想,而是热衷于对大项目的暴饮暴食。当我们越来越感到水资源的匮乏,往往首先向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要效益,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并没有超过先辈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比如说,在我们的治水体系中一直缺乏法律精神与市场理念,农耕文明的体制特征明显,如果不能加以改进和提升,恐怕有多少水也不够用。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向以色列学习。1950年代,以色列出台《水法》,明确国家的水资源是公共财产—土地可以私有,但地下水不能私有—为工农业和生活提供用水是国家的责任,私人用水的权利取决于用水的目的是否合法。他们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由农业部长担任主席的水利理事会,具体制定用水供给标准—不要以为这个理事会是一个官僚集团,它的36名成员中三分之二来自公众,只有三分之一由政府任命。在农业部长负责实施《水法》的同时,政府另外任命一名水利总监,负责监管国家水资源,并设立独立的水利法庭,在水法领域构筑了三权分立的格局,保证了决策机制和行政体系的公开、公正与公平。
在法律框架以内,以色列政府于1960年代实施配额用水制度,对农民在配额之内的灌溉用水免费供给,但超出配额就要高价买水。出于对生产成本的考虑,农民对配额以内的水的使用就会达到效益最大化。在这种供需机制的调节下,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作为战略物资的水资源的稀缺性相对减弱。以色列的经验说明,水资源的需求量并不必然随经济成长而增加,往往是失败的价格机制才带来了当今水资源分配中的种种问题。世界银行[微博]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对许多国家而言,扩增水的供给面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因此往往忽视了水价与需求面的管理,而单方面扩大水的供给会导致生态压力的增加。
所以,我们在争论治水思想的时候,不能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成功的将法治和市场机制纳入水资源的管理体系,这是阻碍我们进一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今后,政府对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安排,以及政府自身在制度体系中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它们的意义要比一些重大工程更加深远。(完)